
蜀山行旅图(中国画)张大千
若有人问起:成都在哪里?
有人说在舌尖上,百菜百味的美食和醇香甘冽的川酒,让骄傲的味蕾不得不频频投降。有人说在茶馆里,一杯茶、一段光阴的悠闲,让行色匆匆的商客羡慕不已。有人说在川剧中,锣鼓声中粉墨登场、穿越古今、笑傲人生,走过岁月的悲欢离合。有人说在蜀锦上,丝的细腻与光滑擦亮了世界的眼。
更多的人认为,成都在画里、在梦里……
纵使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成都,我依然固执地认为:成都在诗里。是那些始于古蜀劳作的号子,源于秦水汉关的平仄,穿越唐风宋雨的吟唱,沐浴明月清风的韵律,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美不胜收、如诗如画的公园城市。
自两千多年前李冰率众修建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造就天府之国开始,成都就注定是一个诗意流淌的城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物质富足、生活安逸,人们才有更饱满而高亢的声音来歌唱生活。因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成都生活为诗和远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成都道教文化底蕴深厚,道家崇尚自由,追求浪漫、师法自然的生活形态又为诗歌的飞翔插上了精神的翅膀。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成都山水形胜、佳境天成,青城山、都江堰、西岭雪山、玉垒山、灵岩山、金沙、三星堆、丹景山、龙泉山、天台山、味江、岷江、锦江……无不撩拨着诗人的思绪,激发着诗人铺天盖地的创作灵感。
如果说美景是诗歌的激发器,那么美酒就是诗歌的催化剂。成都平原得都江堰灌溉之便利,粮食岁岁丰收,人们便用余粮酿出香醉天下的美酒,为诗人的创作加了一把火。所以李商隐醉意朦胧地说:“成都美酒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于是,才有了李调元笔下的历代诗人背琴肩鹤、骑驴载书、泛舟穿峡……“自古诗人例到蜀”!
成都历史悠久,据史可查,它三千年未改城址,两千年不变城名,于是才有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之浩叹。
西汉时,当扬雄从都江堰干渠徐堰河畔的读书台负笈来到成都,他的口吃木讷化作蓬勃的诗情,挥毫写下“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一篇《蜀都赋》打开了文人创作都邑赋的局面,成都因此成为一座被汉大赋赞美的城市。
岁至西晋,左思遍游华夏都邑,有感而发,执笔而作名满天下之“三都赋”,其《蜀都赋》对成都如此写道:“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此刻展卷读来,我们依然可以遥想这位来自都城洛阳、略显骄傲的辞赋家面对成都的富足与安逸时,脸上一定写满了惊讶和艳羡。
唐开国即依靠四川,“倚剑蜀为根本”。李渊建唐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关中饥饿之人入蜀,度过饥荒。而每当唐朝君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都曾把四川作为避难所和复兴地。随之进入成都的,还有诗人王勃、卢照邻、李商隐等,他们与成都诗人欧阳炯、雍陶、尹鹗等声气相通,为中国贡献了大唐诗歌气象的成都华章。
正在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主人公高适、李白和杜甫,都与成都结缘颇深。高适早年郁郁失意,晚岁两度入蜀,平定叛乱,达其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之理想,并赠诗好友杜甫“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青年李白曾在成都生活,仗剑出川后,依然时时梦回故里,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他极尽豪迈浪漫吟咏成都之美:“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一首《春夜喜雨》则展示了成都的另一面。成都之于杜甫,不仅给了他晚年最后落脚的茅屋,更成为他的精神家园,让他在寓居此地时完成了一生中许多重要的作品。同时,杜甫以成都为中心,漫游周遭,写下《丈人山》,“青城天下幽”就得其句“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池。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他为玉垒山所写的诗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和他在浣花溪畔所写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不小心,便成了千百年来吸引人们游历考察成都的最美推介语。而那个叫花蕊夫人的成都女诗人,不仅留下了《宫词》百首,还组织园丁在成都遍植芙蓉,让成都有了一个饱含诗意的名字:芙蓉城。
公元994年,张咏任益州(今成都)知府时,不仅主持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还以诗人的歌喉唱出踏青节(每年农历二月二)的盛景:“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飖似欲乘烟霞。”此后,宋祁、吕大防等诗人皆有诗词与之呼应。
宋时之成都,富庶繁华之极。公元1055年,苏轼第一次从眉州眉山来到成都,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后来,苏轼游历成都,会友讲学、掏钱修桥,为成都写诗:“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此后苏轼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其坎坷流离的后半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成都。但是,只要一提起成都,他总是充满了自豪感,逢人便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成都也成了他思乡的代名词。在他乡,苏轼写下的“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渗透着伤感愁绪。苏轼的《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被认为是他在七夕写给成都的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词曰:“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彩舫。”
陆游在蜀任官时,也把他横溢的诗歌才华献给了成都。回望来时路,他写道“忆从南郑入成都,气俗豪华海内无”;看完海棠,他记下“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赏梅归来,他吟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陆游恨不能时时处处为成都写诗。而他的好友范成大在成都工作之余,不忘诗酒人生,呼朋引伴,游历采诗,于是便有了“海云塔下赏山茶,锦亭燃烛观海棠”“丰年四海皆温饱,愿把欢心寿玉巵”“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绿岸翻鸥如北渚,红尘跃马似西池”……这些美得不像话的诗句,为南宋的成都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明清时期,成都依然是诗歌的热土,各路诗人纷纷来此雅集。当李东阳、方象瑛、王士祯、查礼、顾光旭、窦垿、黄云鹄、张之洞、陈衍、易顺鼎、张问陶、顾复初、王闿运等迈入成都城时,他们的脚步一定押着诗意的平仄。明代出自四川的状元杨慎,大半生都流放云南,却始终惦记着成都,他在《锦城夕》中如此描述成都夜景之美:“锦波澄霁色,丹楼生晚辉。江光二流暝,桥影七星稀。犹明叔度火,未息文君机。南陌骖騑度,东城钟漏微。”
以《圆圆曲》驰名天下的吴伟业到了成都,却发现了别样的诗意:“鱼凫开国险,花月锦城香……万里沧浪客,题诗问草堂。”吴好山以下里巴人的竹枝词写出了清代成都的盛世之景:“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
新文化运动后,新诗发轫,成都亦为重镇。叶伯和、周太玄、王光祈等皆为新诗的领路人。爰及抗战时期,更是天下诗人不分新旧皆集成都,成都为当时诗人提供了“最后的书房”,朱自清、吴芳吉、林如稷、方敬、何其芳、臧克家、常任侠等一大批诗人在此避难、写诗,其中不乏对成都的吟唱。1949年后,在成都创刊的《星星》诗刊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诗歌刊物,多个诗歌流派肇始于此,众多优秀诗人从成都出发,走向全国。
诗歌,经过两千多年的流变与发展,依然是成都这座城市最耀眼的文化符号之一。
今天,正在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成都,公园总数已超过1500个,公园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为公园写诗,为公园城市写诗,为公园城市里的人写诗,也成为今天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这座城市的一种优雅表达。“一城公园半城诗”,是今天之成都最生动、鲜活和诗意的写照。
诗总是与美好的事物相伴相生。在成都,美景是眼中的诗,美酒是流淌的诗,美食是舌尖的诗……在成都,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人居、悠闲的生活和悠然的诗意,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编辑:文静)最新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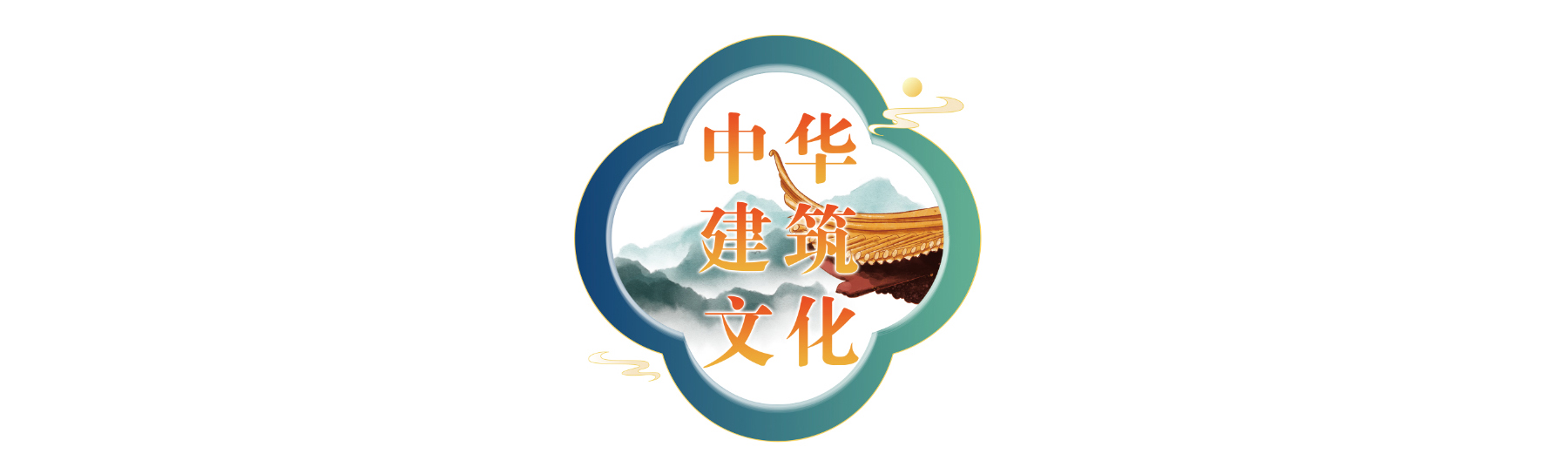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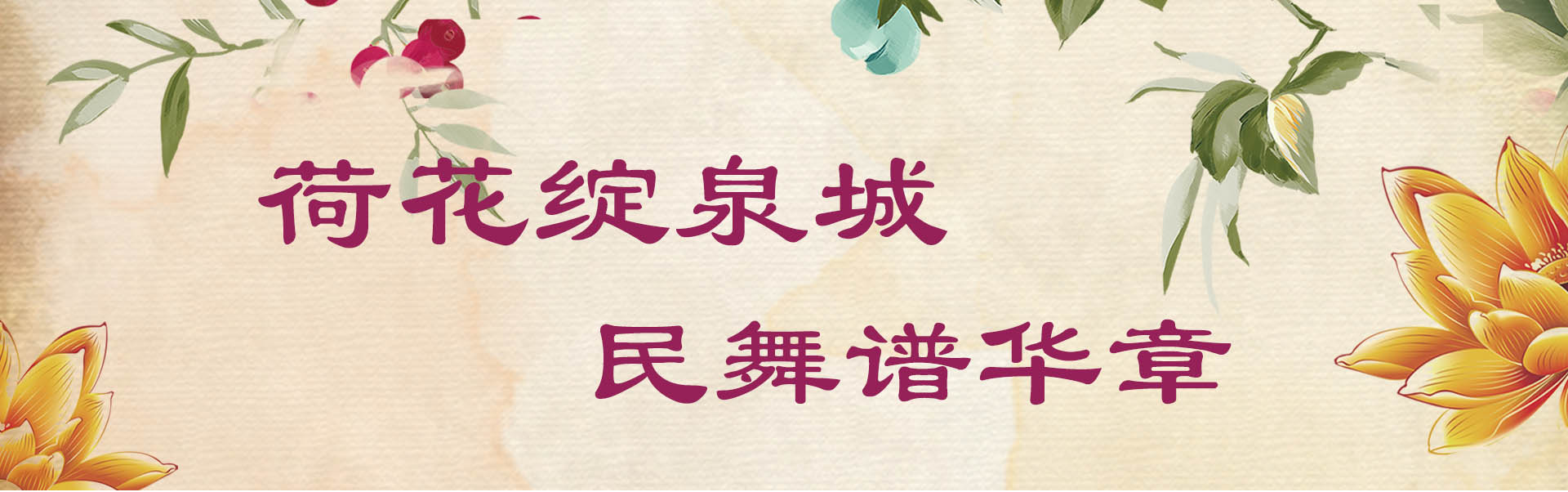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