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中的山雾在青灰的瓦檐上缭绕,彝家小院里那几株石榴树簌簌地抖动着枝叶。只见虬曲的枝干上,淡黄色的石榴半掩在绿叶中,每道裂口上都噙着山风。相传,张骞从西域带回石榴籽后,辗转经中原传入云南,在哀牢山扎下根,逐渐演变成酸石榴。
母亲摘下几个带着露水的石榴,指尖抚过果皮上的褐斑:“这石榴籽抱得紧,颠不散。”她掀起围裙角擦拭果皮,粗糙的指节勾着晨光,像是要把整个哀牢山的思念都揉进石榴的纹路里,塞进我的行囊……2024年秋季,我背着这份沉甸甸的牵挂离开云贵高原,远赴离家3600公里的天山北麓求学。
初到新疆昌吉州的那个傍晚,夕阳将白杨树的影子斜斜地拓在柏油路上,不远处传来热瓦普的旋律。我拎着行李箱站在街角打车,一辆出租车在我面前刹住。车窗缓缓降下时,头戴“朵帕”(花帽)的维吾尔族大叔将头探出车窗:“巴郎子,去哪儿?”他扬了扬下巴,眼角的笑纹堆出沟壑。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巴郎子”是维吾尔语中对小伙子称呼。
我报了学校的地址,随即拉开车门,抱着行囊钻进后车座。两个石榴从包里滑落,骨碌碌滚到前排座椅下。
大叔用“馕言文”开玩笑地说:“你的石榴捧油(朋友),也要付一份坐车钱哦!”他故意把“朋友”两个字咬得很重,自己先被这玩笑逗得花帽轻颤,车内挂着的平安结也随之晃悠起来。
幽默的话语缓解了尴尬气氛,我红着脸捡起石榴,把果子在衣襟上蹭干净,说:“叔,尝尝我们云南的酸石榴。”
大叔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接过石榴,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在他掌心跳跃。“哎——”他突然拖长了音调,花帽下的浓眉高高扬起:“你们云南,也结石榴的吗?”
大叔端详着石榴,开心地说:“看这模样,它和新疆的石榴还是老亲戚。我刚好带着老家寄来的石榴,一会儿也请你尝尝我们的新疆味道。”
车载音响里流淌着十二木卡姆的旋律,大叔随着节拍轻轻晃动着肩膀,花帽下的银发在暮色中泛着微光。这突然让我想起临行前夜,母亲在灶台边哼的彝家小调,两种旋律在脑海中交织……
突然,大叔似乎想到了什么,问我:“云南也有很多民族,你是什么民族?”得知我是彝族后,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在车载音响屏幕上点几下,彝族歌曲《不要怕》熟悉的旋律响起:“阿杰鲁,阿杰鲁……”大叔轻轻地跟着哼唱起来,独特的颤音为这首彝族民谣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车窗外的白杨树在我眼前幻化成哀牢山的竹林,母亲在灶台边哼歌的侧影与大叔晃动的花帽不时重叠……
出租车悄然泊在学校门前。临别时,大叔从后备箱的纸箱里,掏出两个红彤彤的石榴塞给我:“我们管石榴叫‘阿娜尔’,这是我老家院子里的石榴树结的,石榴籽特别甜。”
我捧着石榴,忽然想起离家那天,母亲往我包里塞石榴时的手——原来,云南的晨雾与新疆的晚霞,都偏爱在石榴纹路里藏匿着爱与牵挂。母亲的酸石榴在行囊里生根,大叔的甜石榴在掌心上发芽……
在宿舍的台灯下,我轻轻掰开石榴——新疆的“阿娜尔”绽成浑圆的八瓣红莲,玛瑙籽粒裹着蜜色包衣,仿佛天山融雪凝成的琥珀;云南的酸石榴裹着青铜器般的褐皮,带着棱角分明的六瓣裂口,暗红的石榴籽透着酸涩。再细细地端详,云南石榴籽间缠着银丝般的脉络,新疆石榴里嵌着金线似的纹路……
两颗石榴的影子在桌面上交融,透过褐斑与红晕织就的经纬,我仿佛看见张骞的驼队正从历史深处走来——褡裢里漏出的石榴籽在丝绸之路上生根发芽,有的留在西域长成幸福的甜,有的传向西南化作别样的酸,但它们的根系都深深地扎根在祖国肥沃的土地。
从云南的哀牢山到新疆天山的博格达峰,从云南的金沙江到新疆昌吉州的木垒河,3600公里似乎只是一颗石榴滚动的距离。在我眼前,酸石榴的褐纹与“阿娜尔”的红晕早已不分彼此,就像十二木卡姆的旋律撞上彝族民谣的音符,不同的曲调亦能奏出和谐的乐章。
听,那些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正在中华大地奏响一曲最动人的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编辑:马永)最新新闻
专题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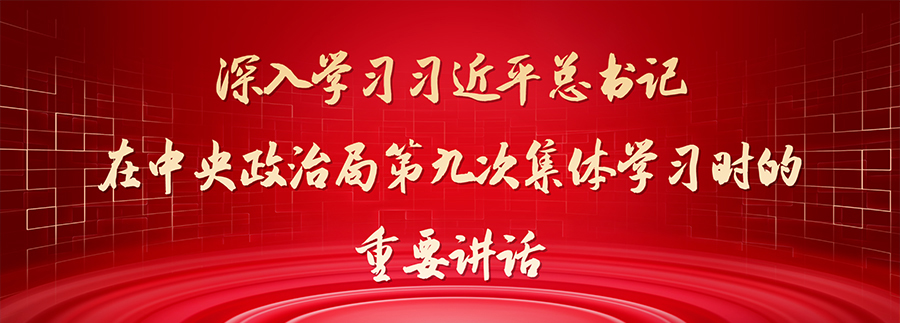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