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势恢宏的土木工程技术到观象授时的“国家工程”,从神秘未解的朱书文字到井然有序的礼制体系,位于晋南黄土地上的陶寺遗址,犹如一处尘封的时光印记,映照着中华文明起源的时空版图。
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物局等单位经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我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更为重要的是,关于陶寺遗址的一系列不间断的重大发现和研究表明,当时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时期,社会礼乐文明初步形成。距今约4300至3900年,以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广泛吸收各地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迅速崛起、走向一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

陶寺古观象台复原。
一 内外两城——城郭之制
1958年,山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在襄汾县陶寺村的南沟与赵王沟之间,发现面积可能为数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陶寺遗址遂被发现。1978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当时的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2002年以来,陶寺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考古进入“新时代”,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通过迄今47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座4000多年前的都城呈现于世。陶寺古城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历史,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依据碳十四测年,陶寺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中期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这是陶寺古城存在的主体年代。
考古工作人员在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面积至少为280万平方米的都城,废弃在今天的黄土之下。2012年至2017年的钻探发现和历时5年的发掘确认,大城之内有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2018至2022年又连续在宫城内发掘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和面积近600平方米的2号夯土基址。至此,陶寺这座都城的“真面目”逐渐清晰可见。
陶寺古城呈现出“宫城——郭城”的分野,城址分为内、外两城,功能分区、等级秩序和空间格局分明有序:从1978年首次发掘至今,陶寺遗址陆续发掘出城墙、宫殿区、宫室类夯土建筑、大型墓地、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和平民区等,功能十分完备。
4000多年前,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数量众多的人群,已经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大城之内的宫城由宽度大于大城城墙的城墙围绕,且有形制特殊、结构复杂、防御色彩浓厚、史前罕见的城门址。陶寺宫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使陶寺“城郭之制”完备,这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宫城内有大量残留的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一处宫殿建筑仅柱网结构就有540平方米。这些细节证明,我国古代都城规划理念在陶寺时期已具雏形。

朱书文字扁壶上的“文”字。

朱书文字扁壶上的另一个字。
二 国宝重器——文明兴起
晋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尧都平阳、禹都安邑和叔虞封唐等古史传说的发生地。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平阳”。而古观象台的发现,也使《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得到了印证。
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古观象台被发掘时,只剩下13块呈半圆形排列的夯土基址遗迹。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求证、模拟观测,初步证实,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特定的观测点和三层夯土台基三部分组成,总面积1740平方米。通过夯土柱间12道缝隙观测日出方位、捕捉运行轨迹,陶寺先民可精准划分20个节令,是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
古观象台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陶寺君王已经能够制定历法、安排农耕、颁行天下。陶寺古观象台建立在精心选址和朝向测量基础之上,正是陶寺先民“逐日而居”的写照。作物的种植与节气密切相关,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观象台,早期的农耕文明便在这里日渐孕育成长。古观象台反映的是当时先进的“科技文明”,是最早的“天地人合一”,也是最早的“问天系统”。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文字扁壶、鼍鼓、石磬、玉兽面以及我国最早的铜器群等许多文物“重器”,同样展现出陶寺比较发达的文明状态。在陶寺早期大墓出土了4件龙盘,它们大小基本相同,盘口直径约35-40厘米、盘底直径约12-15厘米,高在7-12厘米之间。陶寺龙是真正意义上“龙”的雏形,是与夏、商、周及后世龙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龙形象。尤其龙盘上龙口中所衔枝状物或许就是禾穗之类的东西,寓含丰收之意,所表达的是“泽被四方,心系万众”之情,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美德。
朱书文字扁壶是陶寺遗址最常见的汲水器,因壶上有用朱砂书写的两个文字而闻名于世。其中的一个字被多数学者认可为“文”字,争议不大。另一个字颇有争议,目前集中于三种看法:一认为是“邑”字,与大禹有关;二认为是“昜”(音同“阳”)字,与太阳崇拜有关;三认为是“尧”字,自然与“尧王”有关。我们认为,此字上部表示太阳,中间一横表示地平线,下面为“人形”,组合起来表示陶寺先民长期观测从地平线升起的太阳,发现了太阳运转的规律,进一步创造性地发明了观象台,因此此字最有可能是“昜”。但无论为何字,都与观日授时、尧舜时代密切相关。这件残破的朱书文字扁壶,投射出伟大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
陶寺大墓中出土了七大类29件古乐器。其中,石磬以及用鳄鱼皮作鼓面的鼍鼓,是迄今所知同类组合乐器中发现年代最早的。在后来的甲骨文中,“鼍”字正是扬子鳄的形状。陶寺出土的成组乐器,说明礼乐制度已经在陶寺大地上萌芽,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后来逐渐演变为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这些礼乐器的发现,也使得《尚书》“击石拊石”、《礼记》“土鼓”、《诗经》“鼍鼓逢逢”等古老的记载在陶寺找到了实物印证。
陶寺大墓里还出土了一件被认为是文献所载“圭尺”的随葬品,它所测量的夏至日影长度,正是测定“地中”的标准。陶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时期,同时这个国家就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里的“地中”所在,所以推断这个国家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地中之国”,即中国。
陶寺遗址目前共出土了7件铜器及残片,可以明确分辨出器形的是铜环、铜齿轮、铜铃、铜蟾蜍、铜璧等。这表明在陶寺文明时期,先民不仅可以熔炼出纯铜液,而且已经掌握了复合范铸工艺。这种可能始于陶寺的复合范铸技术恰恰是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最核心的铸造技术,创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陶寺时期出现了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这些都被夏、商、周和后世所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诸多流传后世的文明特征,都能在陶寺遗址中找到相应的发端和细节。

鼍鼓(左)及其复原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三 “信史时代”——尧都所在
早在陶寺遗址被发现之前的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汾河流域调查中初到临汾时,就说:“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
今天,经历40多年的考古与研究,一般认为陶寺遗址是尧都所在。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尧或尧舜不仅仅代表某个人,而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时代。尽管我们不能将某一个遗址与具体的“尧或尧舜”完全简单对应,但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
几代考古人证实,陶寺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文明标识与“尧都”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尧”,也会随之走出迷雾重重的“传说时代”,逐渐走向考古实证的“信史时代”。陶寺为尧都所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多重证据,具体包括考古实证、文献印证、民俗旁证、遗产佐证。
陶寺遗址考古学年代上距今4300多年至3900年的时间节点,与陶寺所处晋南“唐地尧墟”空间范围形成了时空之证;陶寺出土的龙盘、圭尺、文字扁壶、鼍鼓、石磬以及观象台遗迹等,提供了与“尧或尧舜”密切相关的实物之证;陶寺巨大城址、宫城宫殿、族群墓地、仓储作坊等都邑要素的出现,与当时的文明状态相呼应;陶寺都城遗址以及周边100余处的陶寺文化遗址分布,与尧舜时代的早期国家及古都相宜。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实证越来越充分与清晰。
陶寺所在晋南是有关“尧或尧舜”文献典籍繁多且系统记载的地方。《尚书·尧典》《尚书·舜典》《论语》《史记·五帝本纪》《周易·系辞下》《周易·昭力》《竹书纪年》等,不胜枚举。甚至文献所言细节如“观象授时”与观象台、“允执厥中”与圭尺、“命质为乐”与鼓磬乐器等都可相互佐证。
民俗是大众对文化传统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可以跨越时空的情感记录。地方志和方言资料显示,山西襄汾、临汾曲沃一带方言称太阳为“窑窝”,实际就是“尧王”的发音。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这种与尧的二女“娥皇、女英”相关的走亲习俗,声势浩大,延续至今。陶寺村“二月二”社火节正是以缅怀先祖尧为主体的民间节庆。霍州清明祭祖花馍“蛇盘盘”也很可能与陶寺出土的龙盘一样,是一种象征与寄托。
此外,在全国各地也都能见到大量与帝尧有关的文化遗产,尤其临汾地区留下了许多传承至今的纪念建筑和名胜古迹,如著名的“尧庙”“尧陵”“尧居”等。这是十分明显的传承遗产,也是一种佐证。
四 文明基因——传承赓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中华先民创造的这些文明品质和精神内涵并非一蹴而就的无根之水,而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仅是陶寺文明,我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各个考古学文化都蕴藏着中华文明基因。
陶寺文明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史前其他不同区域文化因素的特点,至少包括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晋陕高原石峁文化等,集中表现出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文化特质。这种在文化互动中开放、融合、借鉴的品质以及文献所载尧舜时代“和合思想”“协和万邦”表达的互鉴协同、共同发展的精神,实质上正是今天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陶寺社会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更多的是筑城造郭以“卫君守民”、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事等,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领域,作风务实,注重创新。
此外,陶寺文明将创造的物质、精神遗产与理念传至后世,陶寺与河南二里头之间明显存在着传承发展关系。陶寺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而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更广域的范围内传播。陶寺城址明显存在一定的布局规划,二里头遗址同样存在核心区与普通区域的分化,二者包括有宫城宫殿区、祭祀区、墓地、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城址的布局和规划甚至各功能分区的具体地点方位的选择上都有相近之处。大体发轫于陶寺的青铜复合范铸技术传承下来,至二里头时期,再至商、周,均用于铸造以青铜礼器为主的各类铜器,青铜冶铸逐渐达到技术顶峰。
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地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文化融合中,陶寺孕化出一座煌煌都城。陶寺先民在这里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合和万国,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成为黄河流域明确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陶寺文明更是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第五任领队)
(编辑:吴艳)- 前一则: 古诗词中的清明
最新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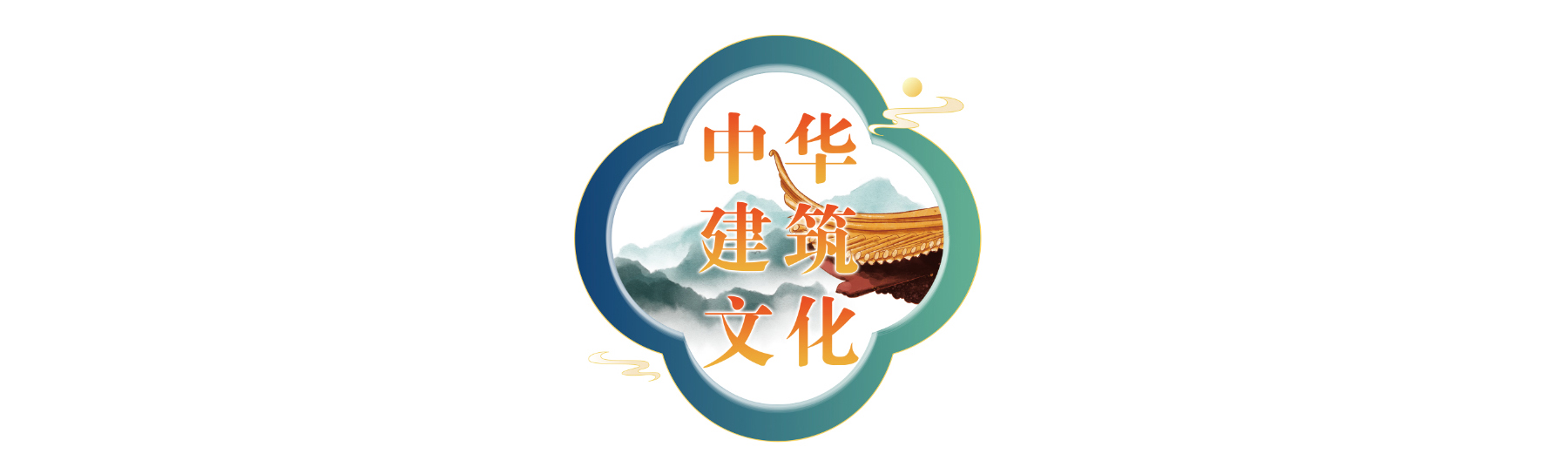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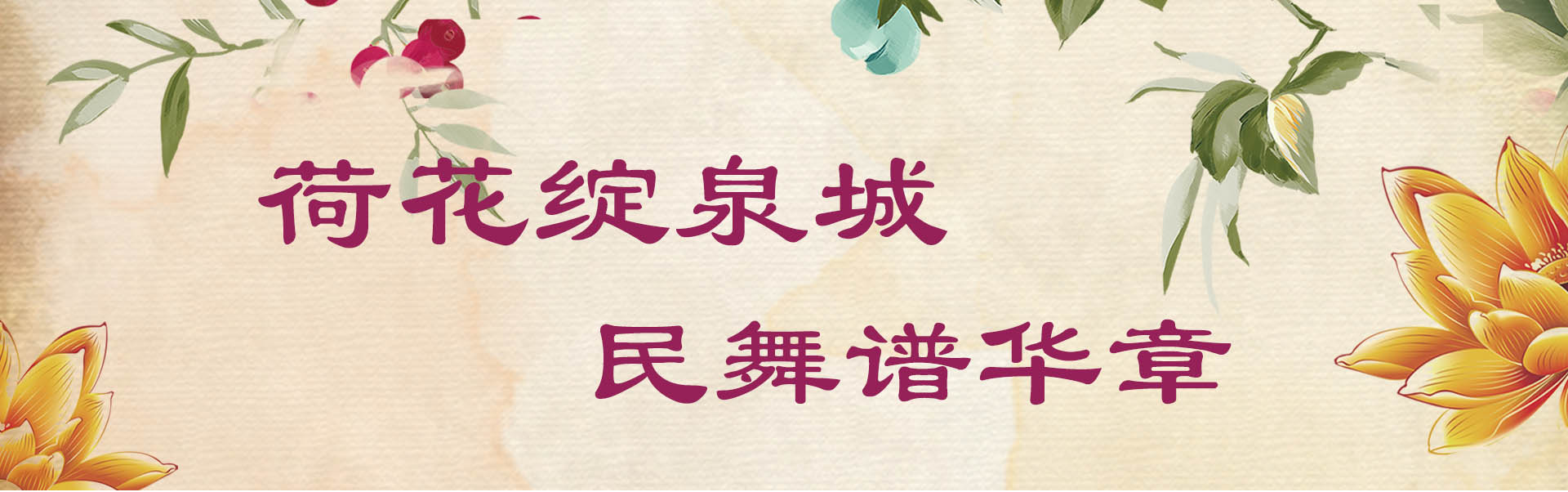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